
 媒体聚焦
媒体聚焦
科学革命是真实的,也是建构的
上观新闻
上观新闻报道 科学革命的起源、发生、过程及其深远历史影响等等,诸如此类有关科学革命的主题,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研究此类有关科学革命的主题,似乎也成了一位成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史家证明自己才华的标配。于是,20世纪以来,有关科学革命的鸿篇著述不断问世,直至今日。

视觉中国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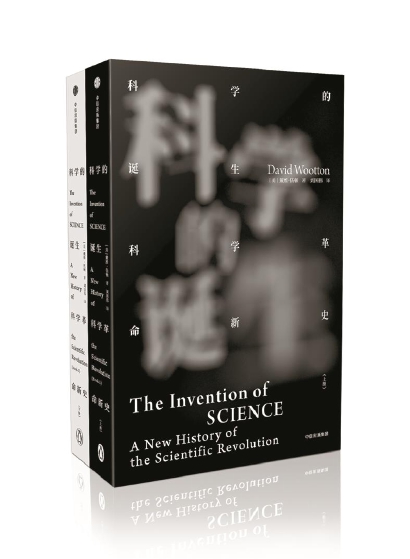
科学史家戴维·伍顿的新著《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是关于科学革命这一常青主题的最新解读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庆桥特为本刊撰稿,解剖这部“科学革命新史”的新颖之处。
现代科学是被“发明”的
戴维·伍顿在开篇写道,现代科学是于1572年至1704年间被“发明”的。
1572年,第谷·布拉赫观测到了一颗新星;1704年,牛顿出版了他的著作《光学》。这种对现代科学革命起源的观点,显然与传统的认识大为不同。对此,作者认为,在科学革命是什么以及它发生的原因上,甚至在是否有这样一种东西上,还不存在普遍的共识。因此,科学革命是如何发生,的确是一个有着极大张力的宏大主题。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解释,而是因为它以数学模式的形式,提供了可靠的预言。之所以把科学革命的起源定义在1572年至1704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历史地来看,1572年第谷发现的那颗新星可能不是科学革命的原因,正如那颗在1914年6月28日杀死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子弹不是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然而那颗新星十分准确地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开始,正如斐迪南大公的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自1572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和人类的能力。如果没有它,那么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以及任何我们依赖的现代技术。
之所以将科学革命的下限驻足于1704年牛顿《光学》的问世,不是因为科学革命此时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到了此时,情况清晰地表明,一个势不可挡的变革过程已经开始。牛顿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初级阶段的终结。
从鸟瞰视角看科学革命
作者不仅深入科学发展史之中,基于原始文献对科学革命的起源给出了新的观点和解释,而且在全书中对百余年来科学革命学说史做出了独到的评论。
在作者看来,科学革命是知识分子从20世纪回望时的一种建构。它模仿的是“工业革命”一词,正如“工业革命”那样,科学革命的思想也带来了增殖和分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存在某种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科学革命的东西的思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一些人主张连续性,认为现代科学源自中世纪科学,或者的确源自亚里士多德。也有不少人寻求把革命增多,例如达尔文革命、量子革命、DNA革命等,这种做法始于托马斯·库恩。还有一些人声称,科学革命发生于19世纪,是在科学和技术的联姻中产生的。在理解过去上,所有这些不同的革命都各有其效用。因此,当论述中涉及某一关键点时,笔者都会对不同的学说给予分析和评价,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该书的思想性。
在对科学革命的解释与用法上,作者认为情况比较复杂。在科学思想史上,“科学革命”一词就在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对杜威、拉斯基和巴特菲尔德等来说,科学革命是一个漫长、复杂、有改造作用的过程;而对科伊雷、库恩等来说,科学革命就是“认识论断裂”,就是知识的突变。作者显然更倾向于前一种解释。他说,如果我们把“革命”一词狭隘地界定为同时影响到了每个人的一种突然转变,那么就没有科学革命了,也不会有新石器革命、军事革命(随火药的发明而来)、工业革命 (随蒸汽机的发明而来)。但是,如果我们想理解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知识、技术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承认延长的、不完整的革命的存在。科学革命就是那种有着非蓄意后果和始料未及的结果的革命,而不是科伊雷所描述的那种彻底的认识论的断裂。
不过,在作者看来,对科学革命的这两种解释并非不可调和。从鸟瞰的视角看,科学革命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始于第谷·布拉赫,终于牛顿。但是,对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来说,如伽利略、胡克、波意耳及其同事,它代表着一系列突然、紧迫的改变。
科学话语的语言学溯源
该书的另外一大特点是,作者非常注重对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关键概念进行语言学、词源学上的解读。思想史的核心关切是语言变化。科学史则是思想史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语言学变化是人们思维方式改变的一种重要标志,既促进了那种改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语言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工具,就科学革命而言,如果没有一种用于思考的新语言的构建,新科学就不可能出现。因此,考察一些关键概念的来历和发展脉络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了。
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家)、自然、发明、发现、机器等概念进行了源流与演变的追溯,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写道,对17世纪下半叶的新科学家而言,他们所处的情况与古典的、阿拉伯的、中世纪的前辈截然不同,他们拥有一种新语言,这种语言让思考新思想容易多了,我现在还在讲着这种语言。这些不同的元素相互支撑、结合,使科学革命成为可能。
在作者看来,语言问题一方面和对自然的直接干预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与广泛的概念、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人们思考科学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是17世纪的一种建构。这一语言反映了科学当时正在经历的革命,但它也使那场革命成为可能。科学名词是在什么时代得以确立其现代意义的,每个科学名词都在现代以前以更原始的含义使用过。科学的诞生史,也是一部科学名词、科学语言的发展演变史。科学语言的明晰与统一,使科学的交流、讨论与传播成为可能。而印刷技术的普及,则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向后看的文化里向前看
作者认为,发现思想是科学革命的先决条件。
科学革命发生之前,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对于推动科学进步具有革命性意义。在哥伦布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是发掘失落的古代文化,而非确立新知识。直到哥伦布证明经典地理学错得离谱,那种认为仅需阐释古人的观点即可的认识才受到了挑战。即使是在哥伦布之后,旧的观点仍逗留不去。从11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欧洲大学教学里存在一种根本的连续性,即哲学是课程中的核心课程,被讲授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历史被认为是重复其自身,传统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指引未来的可靠向导;文明的最伟大成就被认为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存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认为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以及对其文本的传统阐释中找到。就这样,宗教、拉丁语文献、亚里士多德哲学都认为,不存在新知识这样的东西。
哥伦布的发现具有伟大的意义。在一个向后看的文化里,关键的区别不在旧知识和新知识之间,而是在普遍已知的知识和仅为有幸获得通向秘密智慧通道的少数人知道的知识之间。而美洲的被发现,打破了阻碍新知识发现的秘密通道。它是一个公共事件,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凭借这个过程,新知识在一个公共竞技场内确立了其正当性,与旧的神秘文化对立。由于美洲的发现,那种认为一个人永远不该冒险进入未知领域的说法已经变得荒谬,已知世界的边界——赫拉克勒斯之柱越来越多,新发现、新思想的不断涌现势不可挡,新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新工具推动新科学的诞生
在作者看来,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新机器、新工具、新技术的发展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社会生活的祛魅紧密相连。作者着重举了钟表、望远镜、显微镜、印刷机等在促进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在作者看来,望远镜、显微镜对人的尺度感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望远镜对准的巨大空间里,人类突然显得微不足道了。与此同时,在显微镜揭示的世界里,就连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小的生物也似乎很复杂,结果人们普遍想象跳蚤身上也可能有跳蚤,至于无穷。望远镜和显微镜把微粒变成了山脉,又把山脉变成了微粒。通过它们,人们能在一粒沙里看见一个世界,或者变一下,把一个世界看成一粒沙。这是尺度革命,这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对于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对于新科学的诞生,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认为,科学革命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印刷机的影响。16世纪初,印刷革命方兴未艾。我们已经看到了维萨里的《人体之结构》的出版对解剖学的影响。对天文学而言,印刷创造了一个天文学家群体。他们利用共同的方法,就共同的问题开展工作,取得一致同意的解答。
印刷机和望远镜的发明也使科学革命成为可能。它依赖数学和机械哲学,依赖一种新的方法和事实事项的确立。新科学与以前的任何东西都不同。这既是因为它以实验和观测为基础,而非空洞的理论化,也是因为它承认科学理解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摧毁了魔法、迷信和巫术
当然,仅仅有工具层面的进步是不够的,现代的诞生,还是与世界的祛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modern”最初是用来表示“平常的”,其“现代”意义的诞生,则与17世纪以来人们对魔法和巫术的信仰下降有关。巫术属于一种原始的体制,与这个沉着、冷静、安静、理性的新时代格格不入。新科学摧毁了魔法、迷信和巫术。新科学具有节制那些相信天意和奇迹的人的 “荒唐言行”的倾向。
从17世纪末以来,通过布道和讲座,通过通俗文本和戏剧对话,新科学被传播给了数量空前的受众。如果说它在世界的祛魅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话,那么它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因为它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被反复灌输。在这种被反复灌输的过程中,新科学革命就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并不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影响。
科学先行,技术接踵而至
传统的科学发展史认为,科学上的突破总是同步地带来工业技术上的发展,科学被认为是技术的先导,技术被认为是科学发展的结果。这种从科学到技术的线性发展思路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反复言说。而戴维·伍顿却对科学革命的发生与工业革命的进展之间的关系有着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
他认为,新科学与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并不是同步的。在传统上,人们习惯于认为科学革命必然意味着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其实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历史要复杂得多。比如,科学史家研究发现,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还比如钟表的发明制作与普及,水利工程与技术等,它们本身都体现了新科学的原理,但它们都并不必然是科学革命的结果,而是远远早于科学革命诞生。因此,从科学革命到技术革命,到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
然而,蒸汽机的持续不断改进及其应用领域的拓展,却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言,就科学究竟给工业革命作出了多大贡献,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答案是,科学的贡献远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多。工业革命是科学革命的延伸,是新科学的过程、语言和文化向更广大的技师和工程师阶层的延伸。
科学是在1572—1704年被发明的,其中包括研究计划、实验方法、纯科学和新技术的相互结合、可废止知识的语言。我们仍旧伴着这一发明的结果生活,人类好像有可能将永远如此,现代科学思考方式已经成了我们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革命之所以变得几乎不可见,只是因为它已经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
《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
[英]戴维·伍顿 著
刘国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书摘
“科学革命”,一种回望
1948年,在剑桥大学,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开办了科学革命讲座。这其实是大学的历史学家开办科学史讲座的第二个年头。一年前,皇家历史教授G.N.克拉克就开办了这样的讲座。就在巴特菲尔德之前不久,中世纪历史学家M.M.波斯坦也开办了相关讲座。正是在剑桥,艾萨克·牛顿撰写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932年,正是在这里,欧内斯特·卢瑟福第一次分裂了原子核。在这里,历史学家一直承认,他们负有研究科学史的特殊责任。他们也热衷于坚持宣称,科学史应该由历史学家来做,而不应该由科学家来做。
剑桥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接受了相似的教育,拉丁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强制的入学要求。他们在他们所在学院的午餐和晚餐上聚会,但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巴特菲尔德以他的讲座为基础,撰写了《现代科学的起源》(The O rig ins o f M odern Science,1949)。在这本书的开头,他表达了希望科学成为长期需要的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桥梁的愿望。1959年,剑桥化学家、成功的小说家C.P.斯诺发表演说,抱怨剑桥大学的科学教师和艺术教师当时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这篇演讲的题目是“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he Tw o Cu ltu 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 tion)。
在斯诺之前10年,巴特菲尔德采用了“科学革命”这个词。在采用这个词的过程中,他(总是有人说)追随了亚历山大·科伊雷的先例。科伊雷的著作于1935年以法语发表,把从伽利略到牛顿的17世纪科学革命与“最后10年的革命”区分开来。在科伊雷和巴特菲尔德看来,象征现代科学的是物理学,先是牛顿的物理学,然后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们现在可能会赋予生物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不要忽视他们的见解是在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的结构之前提出的。
因此,科学革命最初有两种,一种以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为典范,一种以卢瑟福的核物理学为典范。第一种战胜了第二种,成了科学革命的典范,不过其过程非常缓慢。于是,我们说存在“科学革命”这种东西,以及它发生在17世纪,只是一种非常近的思想。就科学历史学家而言,普及“科学革命”一词的是巴特菲尔德。在《现代科学的起源》教程中,这个词一再出现。但是,在第一次引入它时,他笨拙地让它指代“所谓的‘科学革命’,通常与16、17世纪有关”。“所谓的”含有歉疚之意。更有甚者,当“科学革命”已经被普遍使用时,他还坚持“所谓的”,显得比较奇怪。除了科伊雷的著作,巴特菲尔德是在哪里发现这个词被明确用于描述16、17世纪的情况的呢?“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一词似乎最初是由美国哲学家、教育改革者、实用哲学创始人约翰·杜威于1915年提出来的,但巴特菲尔德不大可能读过杜威的著作。巴特菲尔德的理论来源一定是哈罗德·J·拉斯基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 f Eu ropean Liberalism,1936)。这是一本大获成功的书,1947年刚刚再版。拉斯基是卓越的政治家、当时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有可能爱用“革命”这个词。巴特菲尔德怀着某种不安采用的,应该是拉斯基的用法,而非科伊雷的用法。
因此,在这个方面,科学革命与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不同。就在后两者发生时,它们就被称作革命了。科学革命则是知识分子从20世纪回望时的一种建构。
-
媒体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