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足迹
青春足迹
彭兴滔:故乡的回归——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说起
— 青春足迹自画像:人文学院 研一 彭兴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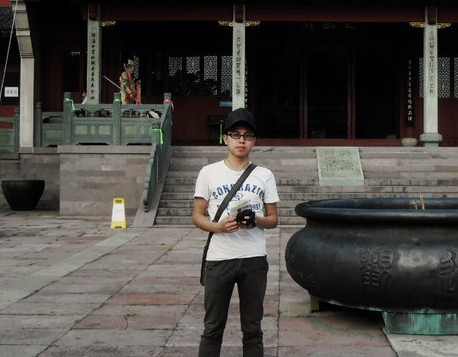
唤醒的故乡
诺贝尔奖可说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复杂情结。就文学来说,从五四新文学时期起,就有不少文人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梦。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也仅仅是个梦而已。据说当年准备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候选人的时候,鲁迅说过,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要考虑中国作家,倘若因为我们的黄色脸皮而颁给我们一个奖,那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没什么好处,甚至是鼓励了青年作家的骄傲情绪。鲁迅这番话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中国作家获奖,倒不是说我们一直徘徊在世界文学之外,也不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落后于世界文学,但不得不说,我们的文学,远离世界文学有点久了。
当马尔克斯借着南美的神秘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的时候,刚从十年浩劫中抬起头的中国作家好像饥饿的孩子寻到了食物的来源:原来我们需要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涯,而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里的故土。于是八十年代兴起了一股“寻根文学“热潮,中国作家们纷纷回到他们带着泥土味的故乡寻找文化的根,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脐带。而莫言,就属于这些作家中的一个。
很多人说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东北乡就如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一样,是一个依靠现实和想象构筑起来的“故乡”。我没去过山东高密,不知道那里是否真的存在一个“高密东北乡”,但我们都切实知道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是作者心里的故乡,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也许现实里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故土,故土的美好和丑恶都只存在我们的心里。我相信,莫言心里的“高密东北乡”就是他的故乡,但不是我们看见的山东高密。
只有回到故乡,我们才能找到自己。因为故乡的人和事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成功的作家就是能把自己熟悉的故事说出来,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很熟悉。换句话说,能拉近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莫言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是山东人,但通过莫言,我们真切触摸到山东高密东北乡那些似乎真实存在过的一切,包括每一丝空气,每一声呐喊。我们都看到了《檀香刑》里赵甲阴郁的眼神,孙丙在城墙上疯笑的脸;也看到了《红高粱》里“我爷爷”光着膀子在夕阳下走远的背影,“我奶奶”在花轿里鲜艳的红盖头。
也许诺贝尔文学奖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奖,不只是把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介绍了世界,更应该看到的是,它给我们,也给全世界带去了一个种满红高粱的故乡,带去了故乡的土地上活生生地站立着的我们的祖辈。
回到故乡之后
莫言给我们带来了故乡。什么叫“带来”?只有失去过,你才会需要“带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作家都没有注意到故乡是那么一个真实的存在,真实得就像在梦里,天天陪伴着,却总是无法触摸。当我们随着莫言的目光回到故乡,我们却成了故乡的一个“外乡人”。于是,故乡在我们笔下,就真的成了“梦里的情境”。很多评论家都说莫言的作品借鉴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换句话就是,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只是梦都发生在熟悉的地方而已。我只能说,有些人看到了教条,却没看到故乡。
藏族作家阿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很多人都把他作品笔下的藏地比作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这只是这些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对于作家来说,那些事情,即使荒诞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如同马孔多在某天下了很长时间的黄花雨,对那片土地之外的人来说或许很不可思议近乎梦呓,但对马孔多的居民来说,确实有过那么一场雨。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也存在同样的困境。很多人都觉得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是不真实的,比如孙丙在城里撒豆成兵,带领一群乡民唱着猫腔与德国军队的洋枪枪炮战斗。之于理性的分析者来说,或者之于用惯了文学理论的学者来说,无论怎么说都有一个理论来套用,但其实对于莫言来说,那就是高密东北乡的一段往事,仅此而已。
莫言是一个不限于某种“主义”的作家,他尝试过不同的写作风格。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用一种“外来”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很本土的故事。而且故事还是发生在一个本土得不能再本土的,几乎只可能在中国才有的一个历史阶段上。当然,时间背景仅仅只是个背景。王蒙开始尝试意识流写作的时候,用的内容也是纯粹的“中国式”内容,也是那段“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方式只是方式,只有灵魂才是真的,而这灵魂,必须系在自己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贴近读者,贴近文学本身。
最害怕的不是找不到故乡,而是找到了故乡,却只会用一种冷冰冰的眼神去看待它。
坚守抑或遗弃
对于低迷的中国文学来说,莫言的获奖无异于一剂强心针,既给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无助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坚持的动力,又给苦苦寻求前进方向的中国作家点了一盏尽管不算明亮却也真实存在的灯。当然,在中国就这样,你能经得起多少赞誉就要经得起多少诋毁,对于莫言的获奖,自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能有助于世界了解当代的中国,了解当代中国作家在写什么,在表现一个怎么样的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只陶醉于曾有过的辉煌,而新文学之后就有点迷失方向。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引进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之后,颇有点茫然无措之感,就像一个穷困已久的人突然看到很多发家的方法却不知道该选用哪种了。于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各种流派异彩纷呈,有的才兴起就消失。而坚持得比较久文学流派,几乎都是从本土汲取营养而试着用西方的文论去解释其创作。在这儿,笔者不想机械套用什么主义与方法去评论莫言创作的得与失,只想说,莫言的成功在于他始终站在一块熟悉的土地上,用最真切的话语讲述一些熟悉的故事。
在莫言得奖之后,中国文学将朝着怎么样的方向努力?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谁也不敢断言说什么方向就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始终无须改变的,那就是真实,立足于故土的真实。这个故土不只是狭义上的故土,更不是说要坚持“寻根文学”的大旗,而是说要忠于内心的呼唤,忠于灵魂的呼唤。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改变不了当下中国文坛疲软的现实,不是我们没有好作家,也不是我们没有好题材,而是这个浮躁的时代总无法让很多人静下来好好思考生命与文学的意义,没有人静下来好好思考除了物质,我们还缺了什么。很多人在这个时代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和失落感,如同一个游子,游荡在无边的旷野上,漫无目的,一直不知道自己少了什么,又要寻找什么。文学不能带给人大富大贵,这是肯定,但当我们静下来想想自己的处境,想想自己为何孤独与空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灵魂缺少了故土的滋润呢?而这个故土,我们就需要回到文学去寻找。
不能说莫言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在当下,莫言带领我们回到心灵的原乡,让我们反思自身,让我们在欢歌或者悲剧之后思考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以至都忘了为什么而走?
所以,我相信,找到故乡不是为了遗弃,也不只是为了坚守,而是在故乡的土地上面向未来,获得继续走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