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大名师
交大名师
张钟俊:中国系统工程创始人
— 交大名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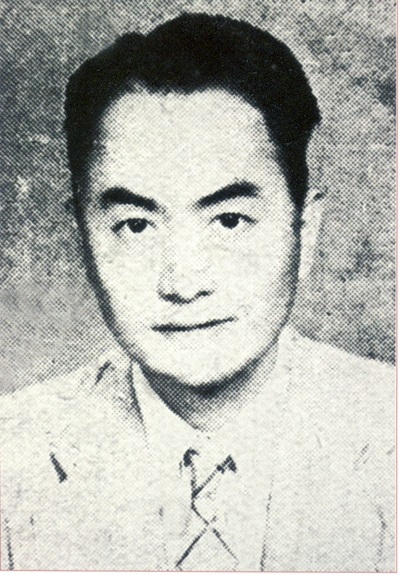
张钟俊(1915~1995),浙江嘉善人。著名自动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同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35年6月获硕士学位,1937年获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1943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电信研究所——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主任。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和自动控制系主任、计算机系主任、电工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所长、系统工程跨系委员会主任和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在网络综合、电信、电力系统、信息自动化等多个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年轻的美国MIT博士
张钟俊1915年9月23日出生于浙江嘉善一个普通教员家庭。11岁为求学而远离家乡,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幼年的张钟俊被誉为“神童”,他博闻强记,兴趣广泛,思想敏捷,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在数次跳级后,1930年9月,刚满15周岁的张钟俊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7月,张钟俊在交大获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因其出众的学业,他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1934年9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工系攻读研究生课程。
MIT是世界著名的工科学府,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科学家,备有介绍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各种资料,它培养学生注重开拓而不是知识的堆积,张钟俊一踏进学校,像扑进了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学习,废寝忘食地钻研,仅用了两个学期即获得硕士学位,随即攻读博士学位。
MIT对于攻读科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要求很高,除了学习本专业的课程,还必须选择一门理学院的专业作为副科,副科要求掌握该专业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知识,还要选学该专业两门研究生课程。电工是张钟俊的主科,他选择数学为副科。在数学系进修期间,张钟俊认识了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R.Wiener)教授。维纳给张钟俊讲授傅里叶积分,深入浅出的讲演,渊博的知识以及杰出的综合能力给张钟俊以形象的启迪。张钟俊暗暗将维纳的治学作风作为楷模,除了听课还时常个别向维纳讨教,讨论的内容常常超出傅里叶积分。这段经历对张钟俊以后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7年12月,张钟俊获得MIT科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刚满22岁。MIT是当时少数几个有权授予科学博士学位的院校之一,对博士学位论文要求非常高。张钟俊的论文题目是《单相电机短路分析》,研究凸极电机短路的暂态过程,这是一个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其中涉及一个含周期变化的参数的微分方程的求解。张钟俊联想到天文学家用傅里叶级数来求解这类周期参数方程,得出天体运动规律的事实,从而大胆地将其用到凸极电机短路的动态方程上,终于获得了成功,第一次在理论上获得了这类电机的一个模态常数。该常数为另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实验所证实。在答辩会上,与会专家对论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文中应用的方法不仅对电机学,即使对数学研究也是一个创新。
1938年,作为MIT电工学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后研究员,张钟俊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协助著名的电讯网络研究专家葛莱明研究网络综合理论。由于他在网络数学理论方面解决了两个重要难题:矩阵(Matrix)和恒正二次式(Defnite Positive Quadratics),因此回国前曾受到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争聘。
后来,他总结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经验,对学生说:“综合也是创造”,鼓励学生要善于综合运用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
抗日烽火中的青年教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次年9月,张钟俊接到家信,得知杭州沦陷,举家避祸于湘赣。国破家亡,张钟俊心急如焚,即日请假回国,取道香港,于10月到达上海。他看到日寇的肆意屠杀,看到同胞沦为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感觉到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张钟俊毅然放弃了回美继续做博士后的机会,回绝了美商要求他在上海电力公司任职的聘请,于11月进川,担任武汉大学(当时已迁至四川乐山)电机系教授,时年24岁。不久校舍遭日机轰炸,张钟俊遂去重庆,任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
1939年底,张钟俊与交通大学校友一起筹建交通大学重庆分校。1940年9月,小龙坎分校成立,聘张钟俊为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2年8月,九龙坡校舍正式落成,交通大学重庆分校成为交通大学总校,设电机、机械、航空、土木和管理5个系。
九龙坡校区位于嘉陵江畔青山之上,远离闹市,环境幽美,但和其他内迁学校一样,物资奇缺。教室里,用土坯垒起或用木料制作成简单的木架,搭上木板,就成了桌凳。张钟俊住的是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仅有一桌、一椅、一凳、一竹书架和一张床。房间窗户朝西,正对着两米开外的大厨房,里面的油烟味一日三次飘入他的室内。张钟俊苦涩又风趣地说:“我最先享受到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
为了培养电信方面高级人才,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等单位资助下,学校委托张钟俊筹建电信研究所。当时,中国抗战军事通讯及后方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大批具有独立研发能力的高级电信专门人才,本科教育难以胜任,研究生教育势在必行。1943年,为了得到各界支持,以便改善经费和设备状况,同时也为了探索与社会用人部门合作,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途径,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吴保丰向交通部电信总局、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单位提出合作培养电信专业研究生的意向,得到赞同,教育部随即批准成立电信研究所。
对于电信研究所成立的重要意义,张钟俊在研究所成立报告中说:交通大学采取与政府机关、企业合作方式培养研究生,“动机在求工程机关与学术界打成一片,充分发挥合作精神。”“查电工机关与学术界之密切合作,在国内尚属创举。反观美国之麻省理工学院在电工方面与奇异西屋、贝尔诸电器公司设立合作学程(Cooperative Course)垂30年,今日该公司与麻工均得驰誉全球,其得助于合作学程良非浅鲜。”
1943年,交通大学唯一的研究所——电信研究所成立,也是我国第一个电信研究所,张钟俊任主任,正式招收研究生,课程设置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随着战争的进行,学校经费逐日减少,机构尽量压缩,教师的工资也都不能保证。然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张钟俊等一批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仍以乐观的情绪,含辛茹苦培养出中国最初的一批电信研究生。
“校企合作办学”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国内高校努力拓展的领域,然而上世纪40年代,交大电信研究所从筹建之初,就已采用了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电信所培养研究生的方案,符合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及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规律,有不少经验值得继承借鉴。
张钟俊等一批教授把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课程内容新而深,能及时反映该领域的世界前沿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网络综合”是当时电路理论领域刚刚兴起并迅速发展的一门学科,也是张钟俊在MIT任博士后研究员时所从事的工作。在主持电信所期间,他不仅自己从事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还指导学生一同探索。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网络综合领域已有不少建树,完成了《电讯网络》著作,专家认为这是国际上第一本阐述网络综合理论的专著。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电讯技术发展异常迅猛,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然而,它对数学和物理学等基础学科却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宽厚的数理基础对于造就具有适应技术更新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的高级电讯人才至关重要。电信所培养研究生非常注重基础理论课程,当年的培养方案中有“高等电工算学”、“近代物理”、“电磁波”3门基础理论课,均开设两个学期,合计为16个学分,占规定总学分数的一半。
电信所对基础理论课程的高度重视,与张钟俊本人的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密不可分。张钟俊认为“工程科学应该与数学结合才能有严谨的基础”,他早年在交大电机系学习时就很重视数学,本科毕业时提出的将数学方法用于电讯网络设计的方案,即因构思新颖而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留美奖学金资助。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解决了电机学上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就得益于他对微分方程和傅里叶级数的透彻理解与灵活运用;他在网络综合理论研究中所取得的开拓性成就,受惠于他在复变函数方面的精深造诣。
从193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位授予法》,到1949年的14年间,全国授予工学硕士学位39名,而交大电信所从1944年至1949年的6年中,培养的工学硕士目前有案可查的就有19名(另一说是30名),几乎占到了全国总数的一半。电信所毕业生质量亦属上乘,交通部电信总局或其他机关对于该所学生均乐于任用,其待遇与国外研究院毕业生相同。这批硕士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电信、电力及自动化方面的高级科技干部和学科建设带头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交通大学由重庆复员上海,电信所亦随学校返沪,中心工作仍然是培养研究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停办。
新中国电力自动化事业的开拓者
1948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张钟俊对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充满了憧憬。他热爱祖国、热爱交大,为建设国家,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继续奋斗。
1945年张钟俊从渝返沪后,即兼任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技术室主任。1949年,他为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市公用事业外商企业单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主持了上海市统一电压和频率、最终并网工程;领导了上海第一条过江电力电缆的铺设,建立了上海的环形电力网。他还针对“二·六”轰炸后上海供电紧张的局面,提出均匀负荷和节约用电的一系列措施,均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采纳。
1950年夏,张钟俊赴长春接洽电信研究所工作的移交事宜。事后他参观了东北三省的建设情形,尤其考察了东北三省的电力事业,当时东北的工业水平在国内是先进的,这次考察使张钟俊对我国电力建设的现状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张钟俊编著的《电工原理》,在苏联教材没有引进我国以前,全国各大学都用它作为教材。他还担任《电力工程》杂志主编,《电世界》编辑,其翻译著作甚多。1952年后,因学习苏联经验和全国院系调整,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指示精神,从我国电力系统方面教育的现状出发,张钟俊决心翻译一批苏联教材,以提高教学水平。自1953年起,陆续翻译了《电力系统稳定》、《电力系统短路》、《电力网及电力系统》、《电力系统暂态过程》和《动力系统运行方式》,还编写了《电力系统电磁暂态过程》,为我国电力系统的教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系列教材,不但在当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而且有的在张钟俊去世后仍被高校选作课本,影响深远。
1956年,高教部指派张钟俊出席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12年科学长期规划会议,为电力组成员。会议长达6个月。在决议阶段,会议指定张钟俊起草电力系统部分的规划。该规划对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电力建设起着指导作用。会议期间,张钟俊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1958年,张钟俊出席中国科学院和水利电力部等4个单位联合召开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技术研究会”,任电力组组长。他亲临实地考察,对发电机的安装、电力传输和电机控制等多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组织领导上海交通大学输配电教研室承担了部分攻关项目。会后,张钟俊着手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立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这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控制系统实验室之一,为解决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电站各种自动控制装置的性能测试提供了实验场所。
鉴于张钟俊在电力界的声望和贡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62年聘请他担任该委员会电力组成员。
中国自动化技术的重要领衔人
自动控制是张钟俊最主要的研究领域,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来他始终站在该领域的前沿。
1946年,张钟俊在研究网络综合理论时,就采用复频率的概念来描述两端口和四端口网络的阻抗,这和当时刚形成的控制理论中的传递函数概念和以后才出现的传递矩阵概念是一致的。1948年,张钟俊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讲授伺服原理,1950年在长春机电研究所又讲授这门课程,这是在我国最早讲授的控制理论课程。
1956年,张钟俊及其助手完成论文《电力系统中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经济分布问题》,运用运筹学方法,首次提出了在各发电厂燃料消耗增益相等时的负荷经济分布的标准,首次提出补偿位置的选择及其配置容量的计算方法,这是我国最早涉及最优控制的论文之一,文中提出优化模型与以后最优控制的提法是吻合的。该文后由科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作为国际交流论文。
20世纪60年代初,张钟俊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卡尔曼和庞得里亚金在控制理论方面的新发展。1962年卡尔曼和布西提出新的滤波设计的时候,张钟俊认识到新的理论已经脱颖而出了。1964年,张钟俊将卡尔曼滤波技术应用到“远航仪”的接收信号处理中,在我国开创了应用现代控制理论的先例。1973年,张钟俊主持潜航惯性导航课题,为此他编写了《矩阵方法和现代控制理论》讲义,向课题组成员讲解现代控制理论,经过两年的努力,该课题完美地结题。设计中,他们再次应用卡尔曼滤波技术对惯性导航系统的反馈信号进行处理,大幅度提高了导航精度。总结该项研究成果的论文《陀螺角速度漂移数学模型的辨识》,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4年,根据控制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张钟俊提出了以大系统理论为指导,以微电脑应用为突破手段、形成分布式计算机控制和信息管理的“工业大系统”研究课题,他勾画了工业大系统的研究框架,分析了这类系统信息结构分散的特性,论述了微电脑的基本控制作用,提出了计算机通讯、协调等一系列柔性生产新的研究方向。
张钟俊带领他的同事们,在控制领域的广泛前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预测控制、鲁棒控制、非线性控制和智能控制等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例如在预测控制方面,他们提出了控制和校正分离的新框架,提出双重预测方法,研究了分散系统的预测控制;在非线性控制方面,他们建立了仿射系统的Yokoyama型,并用于观测器设计和可线性化结构的研究,讨论了非线性系统的分散扰动解耦设计和分散镇定。这些成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具有先进性。
鉴于张钟俊在自动控制理论和应用中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1979年起,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自动化学科组副组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在系统工程研究中卓有建树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张钟俊已两鬓斑白,但他浑身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把所有时间、全部精力都用于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
1977年,我国正从“文革”动乱中走向安定和发展,百废待兴。这一年张钟俊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在发言中,他结合国际上许多成功的范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系统工程的观点、内容和方法,提出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应该推广系统工程,这次发言是我国最早提出应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理论之一。
1978年张钟俊参加了解放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赴美访问团,在45天访问中,到达20个城市,访问了27所大学和20个研究机构,在访问中他敏锐地注意到微电脑的开发和系统工程的应用。在国际著名的策略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张钟俊领略了系统工程在规划和决策中的作用,看到了系统工程实施的全过程,感受到这种方法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这对他在中国提倡系统工程理论的应用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回国后他经常奔波各地作报告,注意收集应用系统工程的成功例子。1980年,张钟俊再度访美,他在佛罗里达大学作了题为“系统工程在中国”的演讲,引起了包括卡尔曼在内的一批科学家的兴趣。
1982年底,上海交通大学接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期发展规划的咨询课题,该课题由张钟俊主持。如果说做报告、写文章是宣传系统工程,那么张钟俊主持的新疆发展规划咨询课题便是系统工程的一次成功实践了。1983年1月,张钟俊率领首批考察组来到新疆,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对新疆的资源、生产、消费和潜力等有一个具体的认识。张钟俊带领考察组成员上午听取有关各方面的汇报,下午整理分析。以后又去各地实地考察。2月中旬,他们带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返回上海,不久,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又送来了他们需要的50万个数据。张钟俊等对这50万个数据作了整理和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建模方针,选取5万个数据作为建立数学模型的依据。又经过半年的努力,描写宏观经济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反映各生产部门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投入产出模型”和用状态空间描述的“动态经济控制模型”3个大型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了,同时完成了一个附属的特尔菲型专家咨询系统。应用这些模型,获得了新疆地区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末能够达到的各项经济指标。1984年9月,张钟俊再次率领课题组到达新疆,向自治区各级领导汇报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各阶段可以实现的目标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次汇报在新疆引起强烈反响,鼓舞了新疆人民的志气,明确了发展方向。《新疆宏观社会经济模型》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建立的大型地区性社会经济模型,这项研究成果获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央领导人的称赞。此后,张钟俊还组织人员完成了牡丹江市、常熟市和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规划的咨询。
崇高风范永远流传
张钟俊是中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的倡导者,为交大的学科建设与培养人才做出了杰出贡献,每逢新年来临之际,他都会收到江泽民同志寄来的贺卡。江泽民于1945年底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选修过张钟俊教授的《运算微积分》课程。张钟俊在科学研究中的大胆求新和培养学生上的宽严相济,给年轻的江泽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工作和学习,多年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张老师的一份特殊的尊崇。
张钟俊讲课从不照本宣科,特别是讲授研究生课程,不用课本,而是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作为讲课的重点。后来,一些在美国进修、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专家,在与张钟俊的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感到很惊讶,这些学生掌握的知识竟然与他们是同步的,都是当时电讯方面最新、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
张钟俊培养研究生讲究“实、严、新”三个字。“实”是基础扎实,他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选读本校数学系的课程,使他们有扎实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他还要求博士研究生有计算机操作能力,这些扎实的基础为博士生单独从事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严”是指推理严格,张钟俊对学生论文都要经过再三推敲,仔细审查其中的逻辑性,对其中出现的“显然可得”这些容易忽视的地方特别注意其合理性;“新”是指选题要新,要敢于接触那些前沿课题,在张钟俊培养的博士中,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以广义系统、预测控制、机器人、鲁棒设计、非线性系统等最前沿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
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张钟俊即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国家设置博士学位后,他又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国家设置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他主持的博士点又首批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自1983年以来,张钟俊培养了126名硕士研究生、34名博士,有12名博士后科研人员,数量上在国内首屈一指。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论文集6卷(其中英文版2卷)。
张钟俊始终在高等院校工作,1990年上海交通大学为他执教50周年(自1940年到交通大学工作算起)举行纪念会,表彰他为培养学科建设接班人做出的杰出贡献。江泽民欣然为老师题词:“执教五十年,桃李遍天下。”
鉴于张钟俊在培养科学技术接班人方面的突出成就,1988年他主持的博士点被评为全国重点,1989年,以他主持的博士点工作业绩而写成的材料《培养高质量博士,推动学科建设》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张钟俊从不服老。1995年,年届80的他虽早已辞去行政职务,却仍像年轻人一样,高效率、快节奏地工作。每天清晨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件,着手修改向交大百年校庆献礼的中英文论文集;每天总有教师和学生来家讨论问题,他仍亲自为学生逐字逐句修改文章。张钟俊深信能在1996年4月8日和大家一起共庆母校百年华诞,他有信心做跨世纪的人。然而1995年12月初,他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讲学归来后,患感冒引发肺炎住进了医院。12月29日,匆匆地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他还充满希望地对女儿说:“明天会比今天好,还有很多很多事要去做。”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