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综合新闻
郑成良教授做客“法学前沿问题”第四讲 聚焦“中国古代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与现代法治”
2022年10月12日晚,法学前沿问题第四讲“中国古代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与现代法治”通过腾讯会议线上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成良教授作为主讲人,对该主题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层次的探讨。
郑教授认为,对法治这一概念的认识,既存在“法律至上”的共识,又存在对“何为良法”认识的分歧。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社会自治是对良法的最低限度的理解。中国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有明显区别,郑教授从学术和语言两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法治”的概念难以成立的原因。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德治”与古代儒家“德治”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由此为法学学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空间以及法学研究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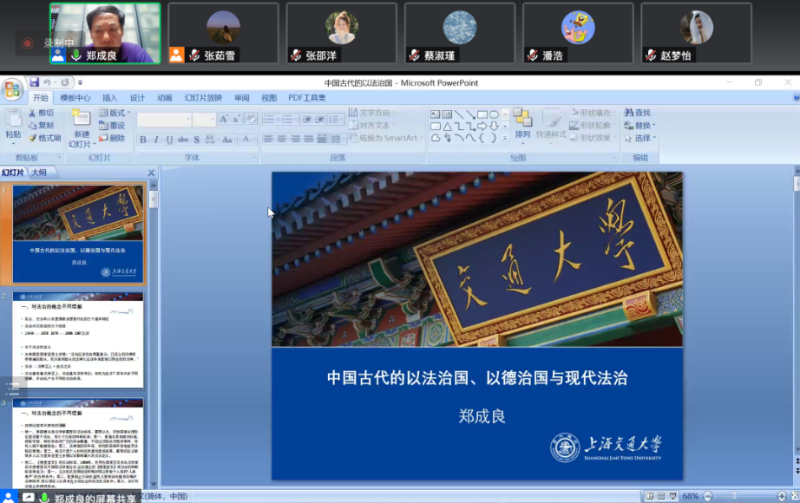
对法治概念的不同理解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和人权。郑教授由此引出“法治”这一概念,并对我国法治共识形成的进程进行了回顾,认为我国法治共识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社会普遍认为法治是资产阶级的产物;1979年至1996年,我国开始有了是否走法治道路的争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自此,我国达成了法治共识。时至今日,经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关于什么是“法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法治包含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但对于“何为良法”,存在着多种理解,因而产生不同的法治标准。目前较具代表性有以下四种:一是英国戴雪的法治标准,包括普通法的绝对权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
二是《德里宣言》认为法治要求立法机关发挥保持“人类尊严”的作用,行政权的合理利用以及实行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三是国际律师协会理事会对法治的标准作出了职业视角的表述,并认为法治是文明社会的根基。四是联合国秘书长在2004年报告中表示:“对联合国而言,法治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个治理原则:所有人、机构和实体,无论属于公营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包括国家本身,都对公开发布、平等实施和独立裁断,并与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保持一致的法律负责。”总之,郑教授认为,对法治的概念的认识,既存在“法律至上”的共识,又存在对“何为良法”认识的分歧。
关于法治的核心理念
郑教授指出:社会本身是个观念的共同体,观念的相通才能使得社会存在。因此,即使对“何为良法”认识的分歧,仍有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社会自治这样对良法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理解。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是区别前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大清朝法律采取义务本位,目的在于控制和管理群众;而现代法律的权利本位,是为了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权利本位把确认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法律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这也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对于正当程序,郑教授认为无论是行使公权力还是行使私权利都必须遵循正当程序,由正当程序追求正当结果应当成为社会共识。关于社会自治,郑教授认为自治和法治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法治理念的思想前提是把社会事务区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范畴,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法律的标准才较多地具有强制性特征,而在私人领域中,公权力不得介入、干预,社会自治就转成了私人自治,在民法上表现为意思自治。社会自治是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其所保护的平等的个人自由。因此,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前提建设法治社会。此三个共识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度不完全一致,但只要民族文化中有这三项共识,或者共识的萌芽,就存在和法治接轨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以法治国与现代法治
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郑教授辨析了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与现代法治的含义与理念。目前,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二者同属法治的范畴;第二种认为,法治概念来源于西方,和古代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不同甚至对立。郑教授认为后者更具合理性,并从学术和语言两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法治”的表述难以成立。首先,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代法治”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是梁启超首次将法家学说用“法治主义”来概括,认为中国古代和西方同样存在人治和法治两种思想。郑教授认为,这种理论既没有充足的数据和调研支撑,亦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只是靠着灵感进行的一种学术推测。同时,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与现代法治有诸多实质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法家的理论是君权至上,而现代法治是法律至上;法家的法律是义务本位(等同于权力本位),现代法治是权利本位;法家理论强调法律是“帝王之具”,是政府手中的工具,现代法治强调正当程序,公权力必须接受正当程序的限制,且程序优先于实体;法家理论认为公权力既可以在公域也可以在私域活动,现代法治强调公域与私域之间有明确界限,公权力越界应受到法律制裁。综上,法家学说和现代法治思想就像甲醇和乙醇,形似而质异。其次,“中国古代法治”概念在语言层面上也难以成立。汉语中的“法治”是对外来概念 (英文rule of law)的迻译。而中国古代并没有“法治”这个词语,只有“以法治国”、“唯法为冶”“任法而治”等表达方式,其对应的英文表达方式是“rule by law”,本质是人用法统治。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实践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是“以法治国,王在法上”,即“rule by law + rule of crowns”,本质还是强调用统治者法律去统治。因此,“中国古代法治”的概念在语言层面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古代德治的理论及其实践
郑教授认为当下人们用于指称现行国家治理举措的所谓“德治”,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德治”是一个有鲜明时代属性的概念,中国古代德治理论上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先王之道”,是指儒家特别崇拜的尧舜禹汤文武治理社会的实践、理论;第二阶段是“孔孟”阶段,是将先王之道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称之为德政;第三阶段表现为“德主刑辅”。从先王之道到德主刑辅,中国德治理论基本成型,再往后的发展都是对这个框架的补充。在基本框架下,有理论的四个基本主张:第一,“圣君贤臣,修德垂范”;第二,“实行德政,敬天爱民”;第三,“教化为主,刑政为辅”;第四,“权在法上,道德优先”。“德治”理论在中国古代的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统治者依照“德治”理论治理国家时,跳不出历史周期率,表现出治世少数,乱世多数。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德治”理论虽然提出了良好的意识形态目标,但没有设置相应的制度保障。圣君贤臣,修德垂范,只能靠君王的个人自觉维持;敬天爱民,对大多数君王而言只停留在口头的宣传;权在法上,道德优先,让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综合来看,中国古代“德治”理论下的实践是不及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