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大要闻
交大要闻
《石子的回响》“文治杯”大学生写作大赛作品选新书出版
2025年4月,《石子的回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36段人生故事,致敬岁月,致敬生活,为我们延展向未知的人生。一个人之于时代洪流或许只是一粒石子,终将被裹挟沉入水底,但在它落入大江大河的那刻,却一样能激荡出水花,发出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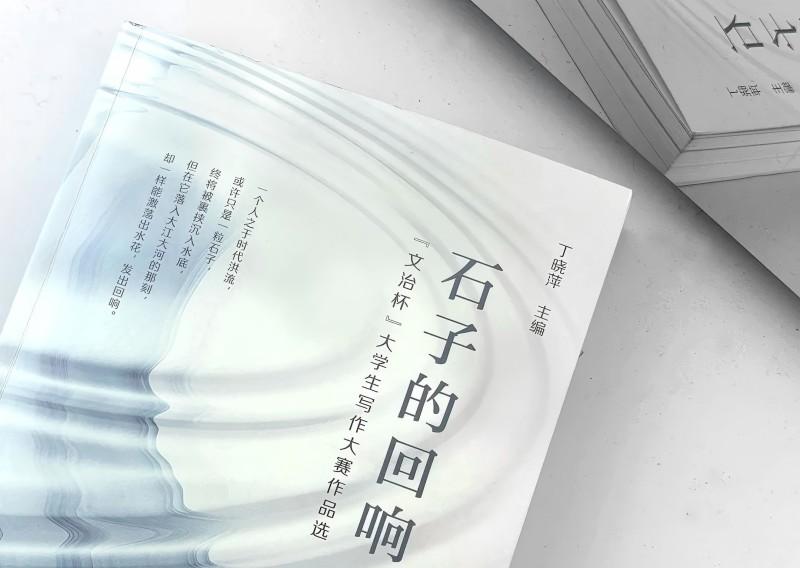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文治杯”是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于1999年为纪念唐文治校长而设的写作大赛,2021年第二十届开始升级为全国大学生写作大赛,由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和《传记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是全国唯一以传记为征文题材的大赛。本书为三年的大赛优秀作品选,分别以“个人与时代”“我的家族故事”“图像中的父亲母亲”为主题,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传记和非虚构写作水准,也体现了当代大学生书写人生的热情与兴趣,融进了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对时代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因而本书可以作为学校传记写作的教学案例、学生学习读本。同时,21世纪是传记的时代。传记与非虚构写作已成为诱人的日常文化实践,因此本书也适合社会上所有对传记与非虚构写作感兴趣的读者。
主编简介
丁晓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编、参与撰写专著及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作为作者之一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获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之优秀通俗理论读物类一等奖和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之普及读物奖。
序:青春的生命写作(节选)
刘佳林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
“文治杯”写作大赛已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多年。2021年起,大赛开始面向全国大学生,并连续数届以传记(生命写作)为征文的规定体裁,主办单位也由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扩展到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2021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2022年起)。这项赛事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参赛作者,逐步为大学生、传记爱好者、传记学界和社会公众所关注。
专业、严格、规范的评审制度,获奖作者受邀分享写作经验的互动方式,是“文治杯”得到积极响应的原因。而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对作者来说,是更进一步的认可与激励。事实上,从2023年起,“文治杯”的多篇获奖作品已经在《传记文学》刊发,分别以“家族生命史的青年视角”专题(2023年7期)和“我们的父亲母亲”专题(2024年11期)成为该刊的封面故事。
现在,更多的征文佳作将结集出版,令人鼓舞,让人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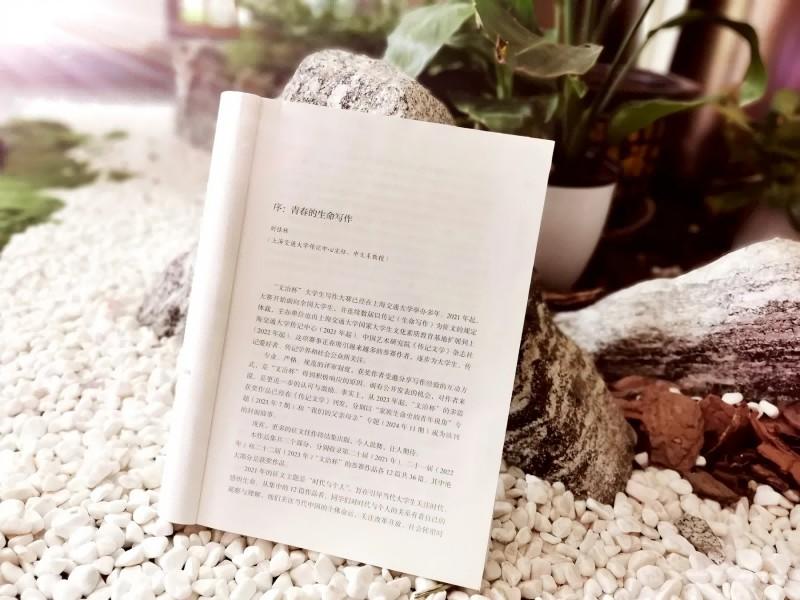
本作品集共三个部分,分别收录第二十届(2021年)、二十一届(2022年)和二十二届(2023年)“文治杯”的参赛作品各12篇共36篇,其中绝大部分是获奖作品。
2021年的征文主题是“时代与个人”,旨在引导当代大学生关注时代、感悟生命。从集中的12篇作品看,同学们对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观察与理解,他们关注当代中国的个体命运,关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劳动者,关注弱势群体,也把自身的发展与追求跟时代、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甚至在历史的深度中追问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表现了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家国意识、人文情怀和思想能力。
2022年的“文治杯”以“我的家族故事”为主题,这对青年作者来说,是一次挑战。因为“家族记忆不仅是族谱里串联的姓氏符号,更是一段又一段充满生命细节、蕴含悲欢离合的人生历程”,家族故事是先辈们的历史,也是后代人的精神泉源,是自我体认的镜与灯。既要准确地再现时代变迁中的家族历史,又要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代际关系,这对同学们来说考验很多。本集中这类主题的作品多从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故事说起,在世代相承的脉络中展开,既放眼大历史,也聚焦家族史,既写峥嵘岁月也写平凡日常,既礼赞亲情也不回避矛盾,深情的叙述中寄寓写作者的反思,颇耐咀嚼与回味。
二十一世纪是图像的时代,传记与图像结缘,既拓宽生命写作的边界,也丰富生命写作的手段,选择“图像记忆中的父亲母亲”作为征文主题,是对数字时代的一次回应。2023年的征文见证了同学们的参赛热情,参赛作品是上一年的两倍。大学生们在用图像叙事或围绕图像挖掘故事方面展示了年轻的优势,他们或者用肩章的变化来叙述父亲的人生,或者用多张照片捕捉父母的生活瞬间,或者借遗留的影像追忆逝去的亲人,或者把故事定格在一幅构图中,表现了构思的精巧。在用图像关联父亲母亲的生命故事时,他们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原来父母也曾少年,原来父母也有青春,他们写父母的苦难,更写父母的坚韧,写父母的普通,更写亲情的珍贵。父母的生命史于他们是一次精神哺育,帮助他们精神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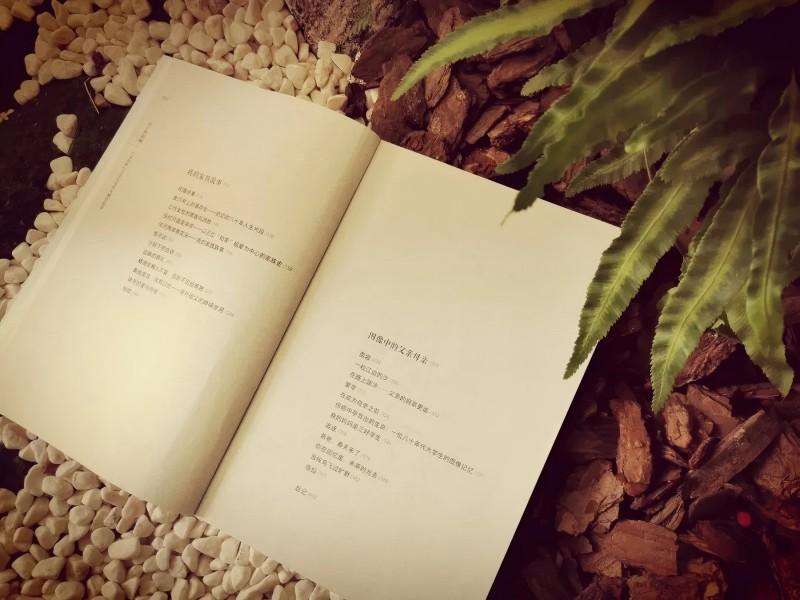
传记以人为中心,要准确、生动地刻画传主,就必须亲近写作对象,深入他们的内心;传记要求真实,要求回到事件的现场,要求求证每一个疑点,因此传记写作往往是不断逼近真相的反复求索。在这些方面,同学们的表现值得称道,令人惊异。他们在采集传材时尽心尽力,他们在观察人性时非常敏锐,他们的思考不乏洞见,甚至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静,他们的笔端又饱含情感,偶尔还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意识。他们在阅读、采访、交流、对话的过程中重建了他们与父母、家族、社会、时代的关系,而他们表现各异的成长期特征,也自然因更多的可能与期待而得到宽容。
……
“文治杯”得名于交通大学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己任,注重德行教育、学以致用,进而提出“一等人才”的理念:“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生命写作通过选择传主、理解传主、书写传主建立与传主的对话关系,是写作者砥砺品行的重要文化实践。以传记为文类要求的“文治杯”征文大赛努力践行唐文治老校长的“一等人才”理念,为青春的生命写作鼓与呼。
2024年12月3日于乐山大楼
《石子的回响》精彩书摘
1. 在隐秘的角落里,也总有办法向着阳光
暖暖让所有的体验者在沙发上坐下,然后缓缓地开口,讲述着她作为一个视障者的经历。她的声音好像一池泉水,在深夜划过岸边的青草。
她说,她并非未曾感受过光明,她的童年五彩斑斓,和我们感受过同样美好的世界;只是疾病渐渐夺走了她世界里所有的光和亮,让她堕入黑暗。
她说,她也曾迷茫过,曾有五年自暴自弃,是家人给予的温暖与包容,让她与黑暗和解。她渐渐发现黑暗其实也是一道美景,让她更能体会到世界的温度。那些看不到的美好,让她沉浸与留恋。
她说,因为看不见,所以可以避开他人的白眼,可以忽略世间的丑恶,可以只专注于自己的本心,与灵魂做最亲密的伴侣。
……
在黑暗中对话黑暗,是平等地体验视障人士的生活。不是同情,也不是歧视,而是感受他们触摸到的世界,理解他们的幸福。那些生动的声音,浓郁的味道,处处透露着黑暗世界的美丽。
……
我们是时候将身体适时地还给黑暗了。
在这个时代,有人生于黑暗,却在内心中升腾出明亮的激情;也有人滥用光明,借以麻痹自己的身心。
——摘自《黑暗中的暖光》
2. 我何以成为我?是谁把我带到了此间?
如果我们将奶奶,母亲,我这三代的经验勾连起来,可以看到在不同年代对“劳动”的定义下形塑出的不同生命。奶奶包含了最原始,最广阔含义上的劳动,妈妈则体验了时代浪潮从公共到家庭生活的过渡,而我做的则是相较起她们而言最“精英”也最狭义的劳动——智识劳动。这三者的链条,理应形成一个闭环,形成共同的“离去的社群”。作为最后一环的我,应当用这种看起来“无用之用”的工作,以不同的形式,但却是同奶奶在相同意义上嫁接起相异的年代和群体之间的联结。而这一联结的主体也蕴含了原始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它像是萨满一样,将自我作为救治的工具,身形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来回切换。把贴近地面之物作为药引,让伤痛的灵魂重回躯体。
——摘自《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
3. 总有人能将生活的苦涩,酿成甘甜
1972年,姥爷进入吉林省“五七干校”学习,并决定利用空余时间提高专业技术——绘画。姥爷主要临摹各种乡村风景图,在新年时这些图画还被印发在师生的贺年卡上,这下子,他每天坚持画画的事迹被传开了。很多人了解不详细,只知道他的工作与绘画大有关联,看他这么刻苦努力,便奉姥爷以美名——“张工作”。
向农民学习,需要亲身下农村,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姥爷从来没当过农民,还真的非常不适应。他的小腿肿了起来,轻轻一按就会陷下一个小坑,很久才能恢复原样。至于伙食,是干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吃饭,一个工作小组会被派到一户农家,与农民们同吃那一成不变的又咸又软的酸菜丝配上大片白花花的肥肉。姥爷很不习惯吃大肥肉,但一个大小伙子不停地干活,真是饿到极致!于是,他夹起肥肉放入口中,不加咀嚼就生生吞下,再马上塞上几大口碴子饭压一压油腻。说到碴子饭,姥爷一顿可以吃光五碗,让所有人都特别震惊。村支书负责派饭,每每派到姥爷所在的小组,都笑眯眯地叮嘱上一句:“‘张工作’要来了,他可能吃呢,记得多做些啊!”
——摘自《姥爷的爱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