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 · 印迹
初心 · 印迹
吴增亮:我在学生时代的革命经历
— 初心 · 印迹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吴增亮(1925-2020年),江苏常州人。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任中共交大党总支书记、中共国立大学区委委员、上海市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徐龙区委书记。1949年后,曾任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指挥,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2011年8月25日,吴增亮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他在学生时代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以及他所亲历的交大地下党领导的几次著名的学生运动。
一 革命觉悟的启迪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我刚满10岁。当时,我的祖父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开办的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秘书,由于上海租界已成为相对安全的“孤岛”,所以他就把一家几口人从常州带到上海来,住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现在叫淮海路。初来沪上的我,人生地不熟,很少与人交往,眼界狭隘,政治上更是无知。直到1939年下半年,我进入上海乐群中学住读,经常与两位同班同学一起做功课,才渐渐打破封闭的交往状态。在相互交流中,我发现其中一位同学常常独坐发呆,心事重重,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学的父亲原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上海沦陷前夕,许多政府官员都有办法携家眷跑到后方,而他父亲却因子女多、家累重,无法离开,但滞留上海后却又很难找到工作,生计很难维持。就在此时,一些已加入汪伪政府的同事又来找他父亲,希望一起共事。这位同学知道此事后,经常苦恼发呆。

交大读书时期的吴增亮
对于这件事应该如何看?我的另一位同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抗日战争究竟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他说自己从报刊上了解到社会各方面的观点,比来比去,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最有道理。即抗战只有靠持久的、广泛的人民战争,通过游击战、运动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夺取最终的胜利。而国民党政府却只靠正规军正面作战,不去大力组织与发动广大人民参战,军队撤退时,连学生与政府职员都丢下不管,这怎么能行?他还以自家为例,提出了妨碍人民战争展开的一些社会弊端。他家是浙江大地主,父亲早亡,母亲当家,靠盘剥地租过日子,平日抽大烟,服侍的丫头一大群,而他家的长工与佃农却忍冻受饥,卖儿卖女……他列举事实,越说越激愤。最后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怎么发挥,人民战争又怎能真正开展起来。
这一席话,是我从未听闻的新观点,同时我又感到诧异:我与他年龄相仿,为何他的见识却高出我很多?他说这是平日不断读书,留心观察社会现象的结果,并因势利导地劝我多看些介绍共产党主张的书籍。从这次不经意的同学对话中,我的思想第一次受到不小震动,特别是他说的“如果中国的青年学生只读学校的书,而不去弄清救国救民的道路并为之奋斗,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希望了”这句话,对我触动极大,至今言犹在耳。之后,我主动阅读各种进步书刊,积极与同学们交流时事见解,初步有了思想上的觉悟。
二 抗日烽火中入党
我在乐群中学读初中时,虽初步萌发了革命觉悟,但由于学校受国民党势力影响较大,政治空气整体比较沉闷,所以在1941年春,我特意转学到当时位于上海的苏州中学读高中,因为这所学校不仅学风严谨,而且进步思想活跃、革命力量强大。例如当时我们班的歌咏活动十分流行,课前饭后都吟唱爱国与革命主题的歌曲,不太看重韵律的优美,旨在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战斗意志。我在一年之中总共学会了几十首歌曲。又如班上还有一个流动图书馆,即把个人买的书集中起来,大家相互交换阅读,读完之后组织座谈会、讨论会,就某些议题展开集体讨论,交换看法。在这段时间里,我踊跃参与班级活动,广泛阅读革命文艺小说。此外,我还受到了小姑妈在革命道路上对我的指引。她也是跟我们一起从常州到上海的,来沪后就读于一所产科医校。当我在“苏中”读高二时,她已经到了苏北根据地,因为她知道的进步知识比较多,所以对我影响较大。
1941年暑假,传来苏北新四军要人的消息,苏州中学有部分人表示愿意去,因为姑妈已在苏北根据地,于是我也报名参加。组织上接受了,分配我做交通工作,即做一名送革命同志到根据地去的联络员。正当我全部送走所有同志,自己也准备赶往苏北之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认为去苏北的人已经不少了,而留守上海的人反而太少,决定让我继续坚持在上海工作,并介绍我参加当时在苏州中学的一个秘密三人干部小组。在三人小组中,我们一面了解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包括经历、家庭、思想、社会关系等,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学了《党章》。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进一步恶化,我就写了入党申请报告。至1942年3月,我被正式批准入党,而令我永生难忘的是当时党对我进行的入党教育。
2011年8月25日,吴增亮接受母校采访(右为盛懿)
由于在我的入党报告中,思想转变多为理论上的认识,缺乏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足够的感性认识,因此,上级领导要求我适当看一些反映革命和阶级斗争实际情况的文艺小说。如辛克莱的《屠场》、高尔基的《母亲》、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我至今铭记于心。其次,是要我了解下三人小组中另一位同志的情况。我通过与他深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同志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因工残就被老板踢出工厂,从此在苦海中度日。以高粱壳磨粉和菜场里的烂菜皮煮粥充饥,就这样还经常维持不了,最后把抱在手中的小儿子丢到菜场垃圾箱边。听了这番遭遇后,我受到极大的震惊,深深感受到旧社会残酷的现实与反动的本质,极大增强了革命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最后,党小组还组织过几次革命与党史纪念活动,如“四一二”纪念会、“红五月”纪念会等,使每一位同志深感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革命事业继承者的重大责任。
苏州中学在日军开入租界后也办不下去了,恰好在我们最后一届高三毕业就停办了。1942年,我面临大学升学,组织上考虑交通大学的党员不多,支部力量还比较弱,就动员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党员去投考。我考进交大的分数不是很高,考分靠前的二三十人算是正式录取的,我是属于预备录取生,当时只有三个人,我是第二名。我祖父当时很不放心,还打电话去问当时的教务长,教务长说,预备生肯定也是全部录取的,就这样才得以进入交大。
三 抗战胜利前后的交大学生运动
我进入交大时,学校已从徐家汇搬迁到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办学,地点在今天的绍兴路上。此时的交通大学已被汪伪政权接管,政治环境十分严峻。虽已建立了党支部,但党组织在校内尽量避免搞较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停止发展新党员,而主要是强调“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党员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为同学们服务,接触群众,与之建立友谊,树立威信,从而有计划地逐个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态度、本人爱好等,因势利导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之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逐步考虑党组织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我和另一位支部成员沈讴(1947届交大运输管理系)负责支部工作,我任支部书记。当时交大的总体情况是:经过我们长期深入的工作,党在交大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群众还未经过大的政治锻炼,不少人对国民党还存有幻想。就在此时,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包括交大在内的上海沦陷区的6所学校为“伪学校”,学生为“伪学生”,必须接受“甄审”,合格者才能继续就读,否则不承认其学籍。这让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气氛的交大学子们顿时陷入义愤和惶恐。这时,党组织就开始在各班活动,推选代表成立全校的学生会,商量解决办法。当时推选出来的学生会主席是周寿昌(1947届交大化学系),另一位学生会干部是胡国定(1947届交大物理系)。这两位同志与我们党员、积极分子关系密切,受到我们一定的影响,所以推选他们出面领导“反甄审”的斗争。
这场大规模的斗争首先是以合法的呈文请愿开始,遭到失败后,接着就诉诸社会舆论,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当时的场面很大,我们打着“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的口号,把教科书、实验仪器等物品纷纷装运到三轮车上,推到马路上,一辆接着一辆,街上行人纷纷前来围观。我们就对群众解释说,车上根本连日文书也没有,怎么能说我们是敌伪学生呢?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为我们主持公道。最后,国民党当局在广大群众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被迫成立临时大学补习班,让交大沪校学生编入“临大”补习班四分部,与其他高校学生一起上课,这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初步胜利。但是国民党还未取消“临大”学生要补“三民主义”和军训课程的规定,因此,党成立了中共临时大学区委,由我出任区委书记,进一步加强对学生斗争的联合领导。当时的“临大”补习班四分部党组织包括交大支部、雷士德工学院支部和南京中央大学转来的部分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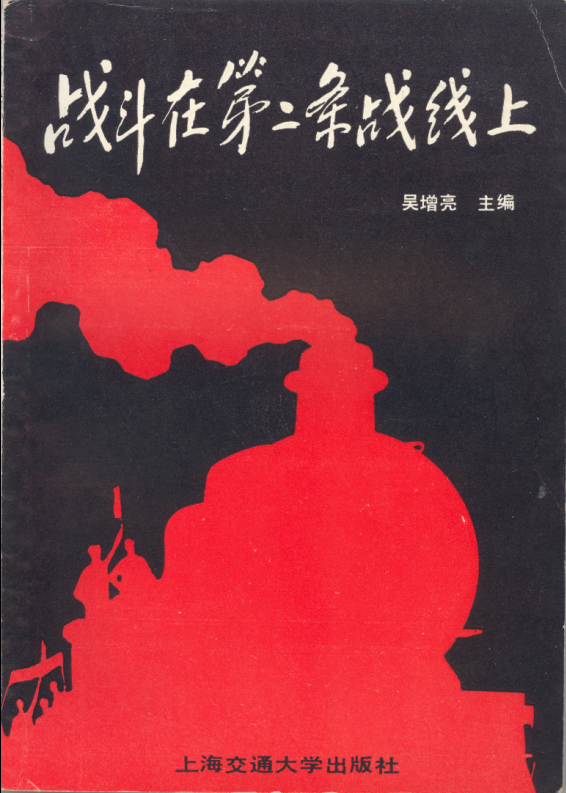
吴增亮主编的《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1989年)
在“临大”补习班开课不久,听说蒋介石来到了上海,同学们纷纷提出向蒋介石请愿的要求。因为当时不少同学对蒋还抱有一定幻想,想通过请愿甩掉“临大”这顶帽子。于是,我们就组织在校同学全部参加请愿活动,在东平路蒋公馆外守候了整整一夜,又冷又饿,蒋介石却始终不予接见,后来知道他从后门溜走了。第二天,报上说蒋介石到国际饭店参加舞会去了,这使大家失望到了极点,对蒋的幻想开始破灭。1946年6月,“临大”补习班期满,国民党派来了几个教官教“三民主义”和军训课。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交大党支部发动群众商量了一个应付之法:上这两门课时,各班只派代表听课,考试时由学生会写好统一答案,大家照抄,使教官无法甄别好坏,借口开除人。这样,学生们经“考试”全部合格,“临大”补习班四分部的学生全部正式转入国立交通大学,取得学籍,反“甄审”斗争终于胜利结束。
1946年9月,反“甄审”斗争胜利结束后,临时大学补习班撤销,其党组织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中共上海市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决定撤销原“临大”区委,“临大”中的交大支部党员、雷士德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的15名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入交大,合并组建交大党总支。由我出任总支书记,沈讴任副书记,受中共上海学委领导。至1947年初反美抗暴斗争时,上海学委决定建立国立大学区委,交大党总支归国立大学区委领导,我任国立大学区委委员,交大党总支书记由沈讴担任。在此期间,交大党组织又领导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校斗争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其中,护校斗争可以说是鲜明地体现出上级党组织与交大党总支的领导智慧和水平的。

1947年1月,交大地下党组织领导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活动。
交大护校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教育经费日益缩减,学校办学经费入不敷出,不仅教师的薪水发不出,有时甚至连粉笔也买不起。再加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排除异己,逼走与他不属于同一派系的交大校长吴保丰,于是大肆削减交大经费,又于1947年上半年强令停办航海、轮机两个系。这种压制和打击,严重威胁交大师生的生存和前途,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护校斗争就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当时的党总支在上海学委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学校与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矛盾,广泛发动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两次教授请愿均未获结果后,党总支决定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系科代表大会,成立了由周盼吾、周寿昌、胡国定等学生组成的护校委员会,发动全校近3000名学生晋京请愿。大家团结一致,冲破了敌人设置的障碍,没有司机,自己开火车;铁路被拆,自己铺铁轨。火车开到真如车站后,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连夜赶来劝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来了,在车站与学生对峙谈判,军警们严密布阵,剑拔弩张,一场血腥的镇压即将发生。

交大护校委员会成员、学生运动领袖周寿昌(左)、周盼吾(右)
在此关键时刻,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专门派上海市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国立大学区委委员浦作赶到现场,秘密找到我,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认为交大护校运动发展到这种程度,国民党必然要进行残酷镇压,敌人已被迫作了一定的让步,再拖下去于我们不利。因此,要党总支不必拘泥于具体条件,争取及时回校复课,尽量不要造成流血事件。根据这一精神,当国民党政府答应不撤院系等基本要求后,总支委员分头到各个车厢向党员和积极分子传达,说服同学们胜利返校。今天回想起来,党的这个指示是很及时、很正确的。当时几千学生在车上坚持了一天一夜,已很疲劳,许多基本要求也已得到满足,再坚持下去会出现很多困难,群众也可能会分裂,而且一校孤军作战,如被镇压下去,对整个蒋管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势头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1947年5月13日,交大护校学生队伍在真如与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对峙谈判
1947年暑假之后,我被调入上海市学委工作,但还直接联系着交大的一个独立支部,它是由交大重庆部分来的党员单独组成的。因为根据钱瑛(当时党的上海局组织部长,领导学委工作)的意见,为防止敌人搞破坏,作更长远的打算,曾考虑过搞两套系统,由我直接领导这个独立支部。不过,时间很短,当年冬天就把关系统一交给交大总支了。我调入学委工作后,沈讴也在当年夏天离开交大,调到上海铁路局去搞全市系统的地下交通工作了。她走后,俞宗瑞(1947届交大机械系)任总支书记。1948年,俞宗瑞调国立大学区委,由庄绪良(1950届交大机械系)任总支书记。这些优秀的地下党员干部在我离开交大之后,继续坚定地领导反独裁、反专制的学生运动,为即将迎来的上海解放而不懈斗争。
2004年5月19日,吴增亮在纪念史霄雯、穆汉祥烈士牺牲55周年祭扫仪式上讲话